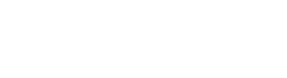专家观点
孙兆霞:扎根田野,仰望星空
来源:社科数托邦 作者: 发布时间:2023年07月27日
近来,中央再次强调大兴调查研究。在乡村研究领域,学者们始终满怀家国情怀,立足乡村调查,致力于促进乡村发展,并构建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
1998年陆学艺先生领导的“中国百村调查”启动,2000年,由孙兆霞老师负责的子课题九溪村项目被批准立项,2005年,项目成果《屯堡乡民社会》出版。20多年来,由孙兆霞老师带领、王春光老师指导的“中国百村调查”贵州课题组一直扎根田野,创新本土研究,并参与乡村建设。
本期乡村研究数据库项目组邀请到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孙兆霞老师代表课题组,分享数十年来基础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与行动研究相嵌构的调查研究经验。
做研究,只要进入现场,就需要多学科和多目标的整合,即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观照下,聚焦基础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行动研究的一些目标和视角。“中国百村调查”贵州课题组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但这四方面结合的研究目标,一以贯之。
从发生学上来说,我们团队的第一个阶段是在198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以下简称“农发组”)在贵州开始第一个规划性或结构性的调研,标志性成果是《富饶的贫困》。1984年,我参与牵头的“山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承接了“农发组”负责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的分课题,对贵州的贫困问题进行研究。
从2000年开始,团队进入第二个阶段,机缘是由陆学艺先生主持、王春光老师负责的“中国当代社会结构变迁·贵州镇宁县”分课题,当时我参与了调查。这个课题做完以后不久,“中国百村调查”开始了。2000年12月,由我作为负责人的“中国百村调查·九溪村”项目被批准立项。当时组建的课题组,从方法到研究内容,与20世纪80年代“农发组”课题是相关的。
第三个阶段,从2009年开始筹划,于2011年武陵山调查时组队,我们这个团队形成比较规范、成熟的组织,研究内容一以贯之。
第四个阶段,从2014年开始,内容转型比较大。包括组织贵州的生态文明与反贫困论坛等会议,对我们团队的成长和工作内容比较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跟当时建立联系的国务院扶贫办(现在是国家乡村振兴局)一直合作到今天。
在推进基础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行动研究相嵌构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一些研究范式和方法上可以对话的经验。
经验一 定位高,立志调研中国国情和中国农村发展
我们团队的研究定位和研究起点应该说比较高。团队的使命感和内在的生命力、生命意义、生命价值的定位,深受“农发组”的影响。
1981年,“农发组”成立大会上,负责人的发言体现了他们的情怀、境界、定位:“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只有人民和时代要求我们站在中国农村发展和中华民族振兴的立场上,按照历史发展的要求,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寻求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战略。”发言最后说:“未来不是宿命的产物,而是人类不断做出选择和进行创造性活动的结果。”
当时分管农村的主要领导杜润生和邓力群也发言了。邓力群说:“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杜润生说:“许多同志下过乡,对农民有阶级感情,阶级感情是我们办好一切事情的基础,它激励着我们去发展真理。同志们,八亿农民期待着你们!”
“农发组”一直参与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从农村到城市等领域的改革。他们建组之后的农村研究从1981年到1984年,从安徽滁县调查开始,还去到西南、西北等地区调查。他们中的一些人直至今日仍在从事农村研究推进农村发展。
1984年,我们直接参与了“农发组”的课题,这对我们来说研究起点很高。
我们课题组的四个人(孙兆霞、罗布龙、田安生、黄永一),1984年7月学校一放假,先到发展组在北京的基地,看到他们的工作状态,很震撼。他们连食堂都没有,天天吃馒头、喝稀饭。我们先上课、看他们的调研报告。培训期间,我们专门到北京大学听取钱理群老师对如何做好项目研究的建议。培训了一个星期,培训内容有耗散结构理论方法、统计学等。记得其中《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性考察》这本书当时很前沿,用系统论来分析中国农村包产到户以后,这个稳定结构怎样被突破。
培训结束后,让我们到无锡农村去调查,虽然做贵州农村研究,但不仅要了解贵州农村,还要了解全国农村的情况。
调查完以后很有收获,一个是对中国农村工业化,尤其是乡镇企业与农业分工,有了清晰认识。当时只知道乡镇企业刚兴起,苏南模式刚形成,但到底什么是乡镇企业,我们在贵州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第二个是粮食问题,当时已经开始抛荒了或者落后地区已经有人到苏南农村去务农了。调查发现这些问题以后,正好遇孙方明老师路过无锡到上海开会,我们一起调查了几天。我们把这两个问题给他反映以后,写了一篇报告《农村内部工农业关系探讨——无锡县前洲乡调查与思考》,在第二年(1985年)的《农业经济丛刊》上发表了。只要是到第一线扎实调研就会发现问题,这两个重大的发现,对我们的学风和专业性的调查方法,具有深刻影响。
1998年,改革开放20年,《贵州广播电视报》(安顺版)跟我约文章,我写了一篇《难忘的感动》,记录的是1984年我们的上述经历及感受。1984年国庆那天正好大阅兵,天安门广场上走过农民方阵。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形象一下子得到极大解放,他们完全是发自内心和来自底层的一种解放感。做研究的人看到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国的农民、为中国的发展起大作用,确实非常激动也非常感动。我们意识到对中国国情和中国发展的研究,应该是我们这代人立志一辈子愿意做的事情。
2011年我们在贵州做扶贫调查,往回看,贵州扶贫实际上与20世纪80年代中央农村政策研究以及基础研究在贵州的落地息息相关,比如王小强、白南风的《富饶的贫困》,以及国务院扶贫办的成立等。
经验二 任何一个研究,一定要有问题意识
当时《屯堡乡民社会》出版以后,人类学研究者说是很好的民族志,社会学研究者说是很好的社会学专著。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问题意识非常强,同时融社会学、人类学为一体的研究。
钱理群先生在《学术研究与乡村建设的有机结合》一文里说《屯堡乡民社会》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是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的,学术研究、文化研究的背后有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乡村改造与建设”的大视野。
徐杰舜在《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初论》这篇文章里,写中国改革开放后人类学能够留下来的几本书的一个重大进展的时候,竟把《屯堡乡民社会》列进去了。2007年中山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上,《屯堡乡民社会》这样一种集中的既具有问题意识也有对策性的研究,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一位台湾学者听完我的发言后说道:原来大陆也有这样一种社会共同体的研究,可以拓展研究得这么好,觉得十分震撼。
我们完成国务院扶贫办的最后一个课题,是2021年独龙江经验的总结。在这个课题中我们提了一个核心概念,叫“扎根的党建扶贫和村庄主体性的关系”。一个“直过民族”在特定生态环境下的主体,如何跨越历史和自然条件脱贫,并且可持续脱贫,实现乡村振兴。这类问题,是西部省区脱贫衔接的共同点与不同点的问题意识,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经验三 扎根式调研,结合发生学的历史穿透性与类型学的结构性
我们团队一直坚持的传统是扎根式调研、扎根式田野方法。
第一点,一定要从发生学角度,做村庄发生学,研究社会如何可能。像屯堡,我们会研究一个一个的村是怎么形成的,经济的、自然资源的、社会的,包括国家体系内部的军事编制等等。
第二点,一定要做类型比较。类型比较和多学科视角的结构性结合在一块,会是一个很好的介入路径。个案调查在类型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学中国化、人类学中国化,从方法上可以对话类型研究、一般性的抽象研究与深度个案研究、扎根式研究。
发生学与类型学之间能够互补。发生学的历史穿透性与类型学的拓宽和拓深,相应地,人类学长期定点的观察与社会学的结构性研究,在更高层面上结构起来。在这些研究范式的体验上,我们团队既可以有一些对话,也可以总结和提炼自己的经验。
第三点,在调研当中我们发明了一些工具。比如村庄资源图,我们调研每个村时,以村庄资源图为工具、导引,结构性的、多样性的关系,纵向的、历史性的穿透力,一张图就可以表现出来。
独龙族原来是在山上,东一户、西一户的,既没路又分散。2018年易地搬迁时,他们有时候开一个会,通知方式是在山下放炮。困难到这种程度,远到这种程度。通过画村庄资源图,一个村有多少座山、多少个农户家,哪一片种哪种树,扶贫以后种草果、喂独龙鸡独龙牛、新开的农家乐在哪儿,都能标注得很清晰。难的是河流,有些溪流是固定的,有些会改道,无数的小溪小河汇合,最后进入独龙江。我们在画图的同时做访谈。如宗世法访谈的时候,访谈对象不知道某个地点的时候就打电话问知道的人,来的人要讨论,互相启发,比如哪里有河、有座吊桥。画的过程老百姓和老领导都会知道,他们非常喜欢我们,跟我们喝酒,送我们独龙族衣服。
一张图做下来,对一个村庄基本上就摸清了。现在的路、小区、公共设施、学校等等,对解决贫困问题和未来发展是什么基础,一目了然。如果要反映中国脱贫攻坚的成果,像这样一些村庄资源图,那太说明问题了。
经验四 面对双重考验,个体有韧性,团队有传承
这四个研究放在一块做,有时候两头不讨好。我们必须要经历双重考验。
什么叫两头不讨好,一头不讨好是在学界。
由于对深度、基层、田野的实际情况不是这么熟悉,有些研究者会质疑,你是在做学术研究吗,难道不是在做政治或者政策工作?我觉得对实践、对国情或者对理论的深度和创新找不到感觉的人,会对我们产生这种误解。
研究者,尤其是年轻人,在学术上还得要往前走,得追求真理性。那怎么说服别人,通过自己的成果形成一些优势,创新空间比较大。我们要有这个底气。
另一头不讨好是在政府那儿。有些政府工作人员会认为,你们学者不就来收点材料、走马观花,回去写文章、发表文章、评职称。对我们的工作和调研看不上眼,觉得知识分子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也会去突破。2021年,我们到独龙江,已经在各村工作了10多天,时间很紧了,想见贡山县独龙族的原老县长。老县长和工作人员观察到我们是在实在做事,被我们的工作感动了。最后我们快要离开之前,跟我们从前一天早上一直聊到下午,第二天下午又开聊,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收不住了,晚上11点多才走。第三天我们团队要离开的时候是早上6点多钟,他又来给我们送行。我觉得这就是理解了、了解了。这些经验也好,考验也罢,只要有耐力、有坚韧性,还是能够克服的。
我觉得如果研究者是单打独斗碎片化调研,不是一个团队,那这些问题都不好解决。经验的传承也好,人脉的传承也罢,都能够稍微消解和化解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