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主题研究 >
调查时间
全部2023年2022年2021年2020年2019年2018年2017年2016年2015年2014年2013年2012年2011年2010年2009年2008年2007年2006年2005年2004年2003年2002年2001年2000年1999年1998年1997年1996年1995年1994年1993年1992年1991年1990年1989年1988年1987年1986年1985年1982年1980年1978年1975年1973年1970年1965年1964年1960年1958年1956年1955年1954年1953年1952年1951年1950年1949年1948年1947年1946年1945年1944年1943年1942年1941年1940年1939年1938年1936年1930年1921年1920年1914年1911年1910年1900年1871年1870年1868年1852年1849年1840年1830年1820年1815年1811年1799年1761年1760年1751年1741年1740年1688年
检索词
-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组织建设与村民治理参与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本报告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湖南省调查数据,分析了乡村治理组织建设的现状、村民治理参与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调查发现,湖南省乡村治理组织建设和村民治理参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多方力量协同困难、村民有效参与不足、村规民约作用发挥有限和积分制推广应用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建议加快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深入挖掘村民自治潜能、优化村规民约和加大积分制推广力度,... -
土地规模经营与生产性服务主体
抽样调查数据显示,随着耕地流转市场的快速发展,虽然耕地经营规模30亩以上农户所占比例不到4%,但其耕地经营面积却占全部经营面积的一半以上;耕地经营规模50亩以上农户所占比例不到3%,其耕地经营面积已占到全部经营面积的近50%,说明当前湖南农村地区农业规模经营已获得较大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湖南农业生产的重要经营方式。在当前湖南农地流转市场上,超过70%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耕地流入方;超过一半的耕地流转行为签订有书面协议,50%的约定了明确租期,契约关系具有一定的规范性... -
灯塔村调查研究后记
本文是灯塔村脱贫调查研究后记,记录了作者与调研组成员前往白河县灯塔村的三次田野调查过程,并对调查过程中提供帮助的单位与个人表达感谢。 -
灯塔村教育扶贫
本文详细介绍了灯塔村脱贫方式之一——教育扶贫。对建档立卡户,白河县和仓上镇出台了针对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种类型的教育扶贫政策,依托产业扶贫培育了“农户+合作社+学校”的产销脱贫模式,取得了良好的脱贫效果。同时也存在着经济补贴方式较为单一、对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关注较少、教育可持续性发展较差的问题。 -
灯塔村调研之背景、内容及方式
本文介绍了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我国贫困的复杂状况、本研究的研究背景和田野选择及本书的写作结构。 -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灯塔村卷——新时代的“三苦精神”》参考文献
本文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灯塔村卷——新时代的“三苦精神”》一书的参考文献。 -
灯塔村社保政策兜底扶贫
本文从阐述社灯塔村保政策兜底扶贫政策的实施机制出发,分析了社保政策兜底扶贫政策实施的主要做法与成效,并提出未来改进的思考。 -
灯塔村金融扶贫
本文从阐述灯塔村金融扶贫政策的实施机制出发,分析了金融扶贫政策实施的主要做法与成效,并提出未来改进的思考。 -
灯塔村就业创业扶贫
本文从阐述灯塔村就业创业扶贫政策的实施机制出发,分析了健康医疗扶贫政策实施的主要做法与成效,并提出未来改进的思考。 -
灯塔村健康医疗扶贫
本文从阐述灯塔村健康医疗扶贫政策的实施机制出发,分析了健康医疗扶贫政策实施的主要做法与成效,并提出未来改进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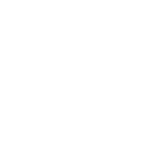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53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532号